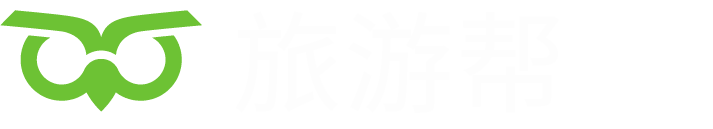到去,从阿姆斯特丹出发。从凡高博物馆出来,天空就一直飘着微雨,我一边冒雨往火车站走,一边毫无意义地暗暗为凡高做着祷告,愿他在天国得以安息,愿他彻底摆脱面包黄油盐巴画笔颜料开销的纠缠。西欧十二月的冷风轻拍着火车车窗。夜深时分,列车停在鹿特丹眩目的新火车站。
从鹿特丹盛名远播的 “(Cubic House)”拾级而上,我预定的旅馆就在它边上铅笔状的塔楼里。鹿特丹在二战时被炸为平地,置之死地而后生,人说鹿特丹现在是现代建筑的实验场,言外之意是它缺乏欧洲引以为傲的中世纪古典美。我在旅馆门口耽了好一会儿,边上两个外国小青年回头看了看我,我们彼此简短致意后他俩继续沉默地吞云吐雾,我则继续无聊地观赏纽维·马斯河的寂寂夜景。

我今夜与一个看上去老态龙钟的、在波兰德国和英国一带摸爬滚打的女人同屋。我进门的时候她只裹着一件大浴巾,对于来路、去向之类的一番互问之后,她开始激动地对我述说她丈夫的不忠行径。她挥舞着一张被她罗列了一堆女人名字的纸张,对我悲愤地控诉那都是她查出的、和她丈夫私通的女人,这里面甚至有她女儿的同学。她说她一和丈夫吵架就会夺门而出,找个地方放逐。她这次的自我放逐地是鹿特丹,这是一个她很熟悉的西欧城市,不过她更熟悉的一点则是,一回到英国,肯定又有陌生的女人在她家里出现。“您也想要我丈夫吗”,她挑衅地问,“您疯了吗”,我没有生气,只是哀其可怜。她亢奋得近乎疯狂,裹在雪白浴巾里的她仿佛一具会开口的骷髅,我深感不安,后来我才意识到她酗酒了。我鼓起勇气睡去,半夜她起身,我曾担心她会把我迁怒于我而把我掐死于朦胧中。我虽担心然而还是继续睡着了。她彻夜未归。清晨7点,我们在餐厅遇上,她似是酗了一夜酒,不仅双目通红,并且精神极度涣散,她已经认不出我了。
清晨,停泊在马斯河畔的船只尚未苏醒,市内的河水也能清澈至此——霞光万丈中,躲在如疏密不齐的旧棉絮的云朵后头的初阳,仍轻易地、且毅然决然地,将近处的威廉斯伯格斜拉索桥(Willemsburg)在河面上印出倒影。从河畔的旅馆出发,沿着河岸行走,日光刺在岸边古旧建筑的窗玻璃上。鹿特丹其实是个半新不旧的、城市风格非常混乱的战后城市,像个睥睨一切的假小子,“阿姆斯特丹,它到底在哪!”——8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鹿特丹人都是在这句歌词的哺育下傲然长大的。



令鹿特丹人傲然的还有根据14世纪鹿特丹神学家、哲学家和无数著作等身的作家埃拉斯姆斯(Erasmusbrug)而命名的埃拉斯姆斯桥,俗称天鹅桥。天鹅桥是世界上最长的斜拉索桥(全长802米),1996年建成后便获得荷兰钢建筑大奖。我从天鹅桥上走,淡金色的朝阳透过拉索,将我的前路映得一片辉煌。十二月底的鹿特丹,没有雪,路面干燥而安全,“德国又下大雪了,日子真灰暗”,我的朋友给我发这样的短信,我很想把在天鹅桥上看到的日出捎给他。


天鹅桥的尽头是无甚看头的高新开发区。


想要一窥鹿特丹过去的影子,我沿河西行很久很久,来到了代尔夫特港(Delfshaven),这里曾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港口,在二战中侥幸逃过德国人的炮火。代尔夫特港还是荷兰海盗史上最著名海盗首领Piet Heyn(1577.11.25-1629.6.18)的出生地,他因为多次俘获了西班牙人满载宝藏的舰队而被荷兰人奉为民族英雄(那时候的荷兰正努力摆脱西班牙的殖民魔爪)。后人为这海盗赋诗写歌无数,登峰造极之作则是荷兰国足在国际大赛前齐唱的那首《Piet Heyn之歌》。

去了趟鹿特丹汉德里克王子。博物馆里,1868年至1896年服役的荷兰海军布菲尔号军舰里、货船复制品里、馆藏的多幅航海手绘地图里,夹藏着驳杂的、光荣的历史的隐喻。荷兰人告诉你,从17世纪起,鹿特丹和上海就建立了阴阳相生、相辅相成的合作伙伴关系——若没有中国,荷兰既不能成为茶叶消耗大户,也无法把代尔夫特出产的陶制小玩意儿远销到海外(说起来这蓝白双色的瓷器还是他们仿中国瓷器做的);若没有荷兰,上海港怎能荣登国际大港;若没有荷兰填海造田这一经典模板,香港人怎会想到在海上搭建个机场——极尽自我褒扬之能事。博物馆极具看头,不过你要学会拨开骄傲看本质,否则你会对荷兰人的高调自吹厌烦至死。
若想要参透鹿特丹人存留于日常中的小乐趣,不妨去趟市政厅广场的集市。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为刺激消费,市集也从一周一次翻三番到了一周三次。长仅500米的街道两旁进驻500家以上的摊贩,这是荷兰规模最大的集市。荷兰特产奶酪、木鞋以及代尔夫特陶器在此都能以不高的价位得手,用点心思和脑筋的话,能淘到颇有价值的古董和实用和观瞻两相宜的的欧式日用百货。